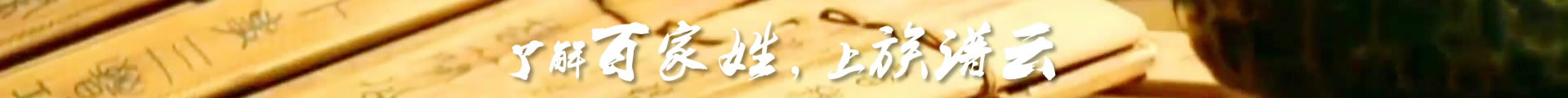文化古寨马滚坡
(发《贵州民族报2012/04/06》)
马滚坡,黔东北务川县的一个小寨,那是父亲的故乡,也是我的根。
这个奇特的地名,源自一个神奇的传说:很久以前,一匹白色的仙马在此下凡,被秀美的风光所迷,不慎失蹄,从寨子南边的白马岩滚至半坡。人们喜爱这匹白马,设法将它送回峰巅,寓之岩壁。那英姿矫健,昂首嘶鸣的形象,引得世世代代的人们翘首仰望。
小寨僻远,迄今未通公路,一条蜿蜒曲折,崎岖坎坷的小路从古代延伸到今天。
马滚坡地名,从小便耳熟能详,但感觉名称怪异,不以为然。父亲也极少提及故乡之事,所以对马滚坡的情况我一直不甚了了。近来读父亲回忆文章,见字里行间充满对故乡山水和文化的一片深情,于是决定借清明之机,返乡祭祖,去看看父亲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。
唐时的杜牧,用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清明》永远地锁住了这个季节的气候,纷纷扬扬的小雨将山路滋润得松软泥泞,迷雾笼罩,高高的峰顶隐匿在天上,我无法看见那匹传说了若干世代的白马。绵延的山脉凸现出座座林木蓊郁的山峰,溪水在峰间流淌,仿佛自天而降。峰峦下面,坡势稍缓处,几十户人家的房屋依山而建,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,随行的亲戚告诉我:马滚坡到了。
一下子,我不由地凝眸注目,打量着这个看似寻常的小寨,心中泛起遥远的思绪。
先祖于何时何地,因何缘故来到这黔东北的大山深处,一直是我心中的欲解之谜,虽然无法彻底考证,但从家谱和旧时碑文中,还是寻到了一些历史的印迹。
曾在一本湖南邵阳的《申氏族谱》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:“元初,某某一支向西北迁至湖广都濡。” 都濡在务川北部,乃当时县名,位于邵阳西北方向,那时,与邵阳同隶湖广。至今,湘中的邵阳、邵东一带申姓者甚众。
务川桃符乡某处,一座申氏先祖墓碑载:“先祖自湖南卜居火炭垭”。火炭垭乃务川一小地名,贵州申姓多源于此。
由此看来,我的先祖是元朝初年而来。当初,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从富饶的湘中来到这层峦叠嶂,虎豹出没的地方?也许是为淘砂炼汞。他们在遍地朱砂的火炭垭落脚,繁衍生息,再由此处分迁各地。三百多年前,一位叫申薄的先祖带领我的族人从火炭垭来到这白马下凡的地方,在新的土地上开垦着新的生活。
申薄先祖居马滚坡至今,已历十一代。若干年来,寨中几乎都是申姓,近几十年方有外姓迁入。马滚坡申氏以耕读为本,崇尚文化。三百年来,这里文风昌盛,科名辈出,清代留下的举人、贡生、国子监、文林郎等墓碑和牌匾比比皆是。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堂烈祖申允继,系乾隆年间举人。他寒窗苦读,求得功名,远仕他乡,先后担任福建德化、大田知县,他为人正直,为政清廉,官声颇佳,其钦敇墓碑联“十闽吏治清如水,九泉幽光朗若天”似可为证。
流连寨中,见旗杆石四下零落,有近十副之多。这是读书人获得功名的标志。明清两代,只有考中举人及以上功名的读书人才能在宗祠、村道或住宅处立此旗杆,上刻某年某人考中何种功名、以及名次,以此光宗耀祖,激励后人。在当时仅二十余户人家的寨中,旗杆石竟如此之多,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。如今,这些东倒西歪的石块早已半埋土中,几乎无人注意;但当年这些石块却支撑着一面面功名的旗帜,昭示着小寨的文化,彰显着小寨的荣光,在这风光秀美的地方描绘出一道绚丽的人文风景。
这里昌盛的文风,代代相传,整个民国期间,全县仅出了十余名大学学子,这小小的山寨就拥有两人,分别毕业于中央军政大学和浙江大学。
寨子南侧,长长的残垣顺坡而上,破败的石阶相伴其旁;石阶边,那株沧桑的古柏树下,静静地伫立着一座高约2.5米的字库塔,八角结构,塔体中空,西面开口,是过去焚烧旧书旧稿的地方。古时,人们视文化为神圣,有“敬文惜字”的传统,凡带有文字的纸张从不随意丢弃,而是集中到字库焚烧化尽。字库塔的修建兴于宋代,盛于明清。马滚坡的这座字库塔建于清道光九年(1829年),字库塔的建立,说明马滚坡虽地处偏远,却曾经是文明教化程度很高的地方。字库塔见证过那段书香浓郁的历史,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先人的惜字之风和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,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家园。遗憾的是,时过境迁,人心不古,如今这座字库塔已经不再收容文字的灵魂。道边古柏葱茏依旧,字库石塔却破旧倾斜,百般寞落地独立在那里。
依次给十几位先祖祭奠,最早的一位,辞世已二百五十多年。那些古旧而不失气派的墓体,斑驳中透出显赫的碑文,记载着他们的辉煌,也记载着马滚坡令人骄傲的历史。今天,马滚坡的后人在各行各业中均不乏佼佼者,但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寨,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却正在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。
与西部地区许多乡村一样,马滚坡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。仅留下老人们在寨子里维持着传统的生计,还有为数不多的儿童。外出的人们攒了钱,便在城里买房子,然后举家迁出,寨子变得越来越冷清。
空落落的寨中,几户人家将收藏的先祖牌位和匾联拿出让我们观看,欣然之余,心中却更加地空落:我眷恋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,但是,那段历史正在被人们忘记。